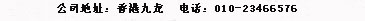我在北京医院免疫治疗
“手术后无瘤存活平均年限是五年。”
这是18岁的李子博高考结束后就要面对的人生困境。为了防止复发,他在北京医院接受了生物免疫治疗,也就是魏则西事件中广受质疑的DC-CIK疗法。现在,医院接受这种治疗。
不过,这个华中科技大学的大二学生,并不是那种人们惯常认为的癌症患者就应该“奄奄一息”、“愁眉苦脸”的模样,他健身、打篮球,参加公益活动,成绩在班级排名靠前,争取未来保研,这是他的自强之路。
在李子博的环境里,癌症患者这个身份,已经不构成任何社交障碍。唯一让他有些忧心的是未来,“就业的歧视,或许会存在吧“。
患癌2年后李子博去免疫治疗前在外游玩
一
我叫李子博。年高考后我被确诊为肾癌。那时我还没意识到等待我的是无尽寒冬。
高考前一直胃疼。因为不想耽误学业,所以我一直忍着难以想象的疼痛,直到高考结束才去做详细检查。在我的家乡安徽亳州拍的片子,右肾占位,那是一团揪扯不清的黑影。医生说,不能再耽误了,你快去北京。就像一场爆炸,我的生活不再安宁。
痛苦!胸闷、气短、胃胀、体重下降。什么也吃不下,对什么也提不起精神。但那时我还心存侥幸,“可能只是良性肿瘤呢?“
医院,非常非常幸运地挂到了专家号,医生的建议是立即手术。然而协和的床位,千金难求。医院外面的“癌症旅馆”暂时安顿下来。三百一晚,漏水的房顶,油腻的墙壁,沉默的一家三口与命运搏斗。旅馆后面就是北京的王府井,灯火通明,过往的人们都很开心。
手术前一天晚上,妈妈收到了短信,电气与电子工程专业,华中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。我很开心,却笑不出来。那晚爸妈特意带我去尝王府井的北京烤鸭,人人都说全聚德的烤鸭天下第一,可我吃在嘴里,总想着“最后的晚餐”,很不是滋味。“好吃吗?”我问爸妈,他们都没有说话。
手术那天,全身麻醉。腹腔被打开,那个邪恶的肿瘤块被切下来送到化验科,我直挺挺地躺在手术床上等待着化验结果。
我以为幸运女神会眷顾我,因为我那样简单快乐努力地活了十八年,心存善意,从不与人为恶,所以这个世界又有什么理由给我的家庭这么大的打击?
可是我没有逃出那个墨菲定律“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,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”:肾癌,恶性。我妈看着18岁的我,恳请医生保住我的肾。如果真的会复发,就把她的肾切给我。
二
医院接受观察。肚子上的刀疤撕扯着疼,我躺了四天,每天只能靠注射麻醉药和吃止痛片才能睡着。手术后第一次下床,连走路都不会了。我妈扶着我,墙撑着我,一步一挪了两个小时,我才基本会走路。
在这段时间里,我遇到了一个接受化疗的老爷爷,一九六几年同济大学电气专业的,也算是我的同门老师兄了。他很坚强,偶尔会和我说一些大学的趣事,让我对于那样自由的生活,心生向往。
其实我向往的不仅是大学生活,还有自己的小爱情。那个时候的小y,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和初恋女友,是我的生命之火,我的希望之光,医院最想拥抱的人。
为了给更多需要手术的人腾出床位,我们一家又住进了“癌症旅馆”。那段时间我每天强迫自己练习走路,强迫自己睡着,强迫自己吃饭。我无比想治好自己,和小y一起开心的去上大学,不再有烦恼。
医院外的“癌症旅馆”过完十八岁生日的时候,墨菲定律再一次被验证了。小y提出和我分手。我求她不要这样,我求她等我回亳州再说。我的手术伤口没有愈合,我身上插着导尿管和排积液的硬管,面部浮肿没有血色,我就像一只大怪物一样。没有回家的车票了,我央求妈妈让我坐连夜十个多小时的硬座回家,我要去找她。
可是我连她的面都没见到,就这样被狠狠地踹了。我不记恨她移情别恋,事故复杂,因为没有用,因为我知道,电视剧里面的不离不弃和生死相依大多都是假的。“正常人”对像我这样的癌症患者都抱有无尽的同情和鲜明的恶意,在他们的眼里,我们是可怜的,我们是负担,是快要死掉的人,是没有未来的。
失恋后的某天,我和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在亳州的ktv忘情的唱歌。我说,我得癌症了,他们笑着不信,“你带球上篮我都防不住,就你还癌症,别逗我了。”但是我的右腹蜿蜒十五厘米的伤口为我做了无声地辩解,大家唱歌的气氛变得不太一样。这个时候妈妈的一个电话打破我们这种强颜欢笑的诡异氛围,她让我快回家收拾,当夜的火车去北京,第二天接受化疗,医院。
三
化疗,我懵逼了。回家的路上,我想哭,那是我这么长时间乱七八糟的生活而第一次真的要哭了的时刻。我以为,我不哭我咬牙忍痛接受手术我就永远的告别癌症,就可以和兄弟们一样去大学了。
没有人告诉我需要化疗,因为在我看来化疗无疑宣判死刑。妈妈说,成人型肾母细胞瘤,恶性一期,发病率千万分之二,手术后患者无瘤存活平均年限是五年,而且这五年里癌细胞复发和转移的概率不低于百分之五十,在手术后一周内化疗最有效。
我妈在家看了十几年的修理铺,第一次用这么严肃专业的语气和我说话。没有挣扎的理由和力气,我又踏上了去北京的求生之路。人流滚滚的北京西站,只剩半条命的残喘少年。我真的,好怕死亡。
那是我的十八岁,暴瘦二十斤,等待我的还有两周一次的化疗,每次持续一周。化疗是真的很难受很难受,生不如死。
化疗后我还要大量喝水防止膀胱炎,所以在吐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我还是要大量喝水,在恶心到抵制进食的时候还是要大口吃饭。头发几乎落完。化疗的药水,脂质体阿霉素,进口药,一瓶六千,一次三瓶,每期化疗都要花费三万多,不能报销。我不知道我普通的家庭还能坚持多久。我的右臂上有一根PICC(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)顺着大臂,直插心脏,输送药物和希望。
前两次化疗的时候我还在想,我要撑住,我要在暑假完成化疗回去上大学。但是第三次化疗后回家的路上,我终于受不了了,崩溃地在妈妈身上哭了起来,我也知道,这个学,我是上不了了。于是我去学校办理了休学,给我刚见面就要分开的大学室友说,“等着,明年老子李杀神一定会回来的!“
四
六次化疗最后终于还是结束了。可是我还要去北京医院,继续生物免疫治疗,也就是后来广受质疑的DC-CIK疗法,说是能抵消化疗的副作用,也能更精准的杀死癌细胞。(魏则西治疗的“免疫疗法”究竟怎么回事?)
第一次接触这种免疫治疗,是在化疗之中,爸妈问医生有没有其他治疗的方法,医生说:有一个细胞免疫治疗,作为预备治疗方案,不一定有作用,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。
在我化疗后妈妈就去医院咨询,医生说是对化疗后身体的毒性有减轻作用。爸妈想着我做了这个应该更保险些,于是就让我做了,而且这个生物免疫治疗对肾癌效果很好。
当时的治疗方案是第一次隔一个月,随后隔三个月做一年,再往后隔四个月做一年,再隔半年做一年,最后一年一次。而每次要持续两周,第一周采血培养细胞,第二周回输。
因为一期的费用超过三万,我问爸妈:“大家都说这个免疫治疗是骗人的,而且还这么贵,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。”爸妈说做治疗总比什么都不干来得好。所以一边安抚我让我安心治病,一边掏空家底。
于是在年12月就开始了第一次治疗。医院,找到主治医师,我就躺在旁边有个过滤血液的床上。双臂都插上管子,一个抽血,一个输血,机器从中过滤所需的细胞。整个过滤过程大概持续有一个半小时,其间他们让我不停捏手里心状的小球,应该是加速血液流动用的。整个过程除了有点无聊,手臂采血时候有一点点痛,其他相比手术和化疗来是轻松太多了。一周之后,来到病房回输细胞。
治疗期间,遇到很多病友,有的说帮助控制了病情,有的说心里没底来试一试。谁知道呢,毕竟大家都没有恶化复发,不知道这个疗法到底起了多大作用,当然了也不想复发。
同一个病房的病友也是天南海北,年龄跨度很大,而且患的不是一种癌症。我想我的目的就是预防复发,而我现在手术化疗后的康复情况还算不错,就一直主动联系医生做了下去,这一做就是两年。
年魏则西事件出来之后,这个疗法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直接的效果是,费用降低了,现在是1万多。我在知网、知乎上看到过各种回答,总结起来中立的说法就是“可能会有效果,不同人不同反应”。意思就是,效果不稳定,不像传统的手术、化疗、放疗一样有确定的效果和丰富的经验。
后来继续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dgzhengxing.net/wzqdyy/6422.html
- 没有推荐文章
- 没有热点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