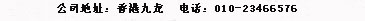赵聆我们家的良师益友纪念最亲爱的周先
作者赵聆与周广仁(左一)、妈妈凌远(左二)、爸爸赵屏国(左三)孙楠/摄
3月7日,当我正在全力准备和安排爸爸3月8日的安葬仪式时,噩耗传来——我们家的良师益友,最亲爱的周广仁先生离开我们了。
瞬间,朋友圈被“覆盖”了。
记得去年3月5日这一天,我收到周先生的儿子陈达的留言:“哎聆儿,看到朋友圈,赵叔叔住院啊,情况不太好是吗?我妈妈这边也是一直比较危险,你一个人悠着点儿啊,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打个招呼!……”之后每次见到周先生女儿小涟姐姐,妈妈和我都会关切地问起周先生的近况,听上去不错,我们一面替先生的状况而高兴,一面继续为先生的健康而祈祷。但最不想看到的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……
妈妈为她失去了她最重要的、最亲密的良师益友而深感难过,他们并肩作战共同奋斗建设了中国的钢琴事业。
音容笑貌,往事历历在目,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
友谊常青
年,妈妈八十岁大寿。周先生给她写了一封贺信:
“亲爱的凌远:
今年是你的80大寿。我祝你健康,长寿,永远幸福!
时间过得真快。记得我年到中央音乐学院跟苏联专家进修的时候,你是从印尼来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爱国华侨。那时候,我们俩都是二十几岁的热血青年,我只比你大四岁。在钢琴系的学习演奏会上,你那乐感和热情洋溢的演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新中国成立初期,学校虽然条件很差,但是师生的学习热情及团结友好的气氛是终身难忘的。你毕业后,就到附中去任教。那个时代,学校总是把好学生放到附中去任教。你是附中教学队伍中的元老了。
你的教学成果是大家都公认的,你桃李满天下,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。其中最突出的是王羽佳。
她已是世界级的钢琴家了。这跟你从小给她打的基础分不开。这是你的心血,是你的光荣。在教学上,你刻苦钻研。年我搞师资培训班的时候,我请你来讲学,你介绍了全套门德尔松的《无词歌》,赵屏国老师介绍了柴科夫斯基的《四季》连讲带弹。你们二位给教师们作了榜样。
我们这代人,经历了风风雨雨几十年,但是我们两家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。记得我们住在筒子楼的日子吗?你们住一层,我们住在二层。我们的孩子们每天都在一起玩。我们能听见你们房间里传出来的父母和儿女们四手联弹声。在我那小小的房间里,三角琴上我们还经常开家庭音乐会呢。小聆子是你从小自己培养的。到了毕业班的那年,她来到我班上。她是一个孝顺的好姑娘,我也很喜欢她。我们为了中国的钢琴事业合作了许多事情,从办‘星海少年儿童钢琴比赛’到编考级教材,始终我们都是一起干的,而且干得很愉快。
我们的友谊常青!”
童年时周先生家的三角琴
赵聆和周广仁一起演奏四手联弹其实,音乐界圈子很小,低头不见抬头见,更何况我们都住在同一个院子——中央音乐学院。我们住四号楼一层,周先生住在二层把角儿。
爸爸妈妈他们同事之间都亲切地称周先生为“周先”或“周广”。
应该说,我们跟周先生的音乐生活是“连”在一起的。因为住得很近,而且周先生很愿意把她知道的东西分享给我们,所以她总是带着我们,愿意给我们讲一讲、听一听。
说起周先生的家,那时候全院只有周先生家有一台又好看又好听的Blütner(布卢特纳,现译名博兰斯勒)三角琴,琴上都是雕刻的花纹。周末,爸妈和哥哥会带着我到周先生家听(弹)“周末音乐会”,不定期还会有不同的老师参加。去先生家的每一位都可以参加演奏。那大概是我人生第一次参演的音乐会,人生第一次互相听、相互交流、互相促进,督促学习。甚至我人生的第一次弹三角琴都是在周先生家实现的!房间很小,可那情景在我记忆中真美好,氛围特别温暖。那时候,我哥哥赵威和黄青、王凯、周先生儿子陈达是音乐学院子弟中的“铁哥们儿”,是热爱音乐的狂热分子,一起“发烧”音乐。陈达是评论和欣赏家,很具有煽动性,感觉特好,特能侃;黄青是作曲家的儿子,不仅提琴拉得很好而且耳朵非常尖,能听到很多乐队的内声部;王凯是忠诚的听众,后来在乐团里兼大贝斯;我哥赵威是钢琴演奏家,机能和爆发力非常好,什么都能“海”,上手特快,特能弹。“黄河”“老柴”加乐队交响乐的东西,无一不碰。所以四个人在一起很是热闹……他们就这样,说一段儿来一段儿,每天为音乐持续“嗨”。
对我而言,我们的老四号楼、周先生的家,是我从小受音乐熏陶、开始喜欢钢琴、喜欢音乐的中心,是“根据地”。
从小遇重大活动或演出、比赛前,妈妈总会请周先生听一听我弹琴。每次周先生都会真诚充满慈爱地说:“弹得很好,姑娘!”总在鼓励我。
我从附小就开始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,那时候,周先生总会不定期在学校的录音室,为大家播放她从国外带回来的音乐频道的录像。其中有很多钢琴家们的音乐会或访谈,皮尔斯纯净充满金属声的莫扎特、年轻时刚出道的佩拉西亚漂亮灵动的舒曼幻想曲集……有英文的、德文的,周先生会在一旁做同声翻译。
这种持续的活动为我们大家打开听世界的耳朵、听觉和审美。先生是在培养会听音乐、有求知欲、有追求的我们。
教钢琴厂的工人弹琴
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,我上大学时,周先生教我们钢琴教学法。其中的实践课由周先生带着我和另两名同班同学去星海钢琴厂,教制作钢琴的工人师傅们弹钢琴。
记得当时的星海厂在大北窑,挺远的,每次坐公共汽车来回都会在黄土飞扬的北京城变得灰头土脸的。
第一次走进厂房,巨大空旷的车间里排满了一台台、一排排的钢琴。我们从第一台琴开始弹,一溜音阶弹到最后一台,没有一台的触键相同,参差不齐深浅不一,音色就更别提了。
我们要教会工人们弹琴,让他们分辨钢琴的触键,慢慢会听什么样的琴声是好听的。班上的工人学员年纪不一,个别师傅的手上是厚厚的老茧,骨骼僵硬,大多都是白丁,不认得五线谱。
经过几个月每周一次的钢琴课,汇报演出上,每位学员都背谱完整演奏了两首乐曲。
现在回想起来,感触最深的是周先生的远见和胸怀,她带着我们做了一件既有意义又有创举的事情:既普及培养了工人们,让他们通过自己学琴,变成有感觉、有知觉、有分辨能力的工人,又可以通过对他们的改变,提高钢琴制造的质量。
去年我无意中翻到合影寄给星海厂领导时,他告诉我,几乎所有当时学琴的工人都已经退休了。
周先生总是想尽办法普及钢琴教育,为大家学懂音乐开启大门,被称为“钢琴妈妈”。
敬佩!感慨!
亲老师——
无限耐心的老师
本科毕业音乐会后,赵聆与周广仁(左一)、妈妈凌远(右一)合影
年,本科毕业那年,我转到周先生班上。
周先生上课时态度温和,说话轻声慢言。她会建议我可以这样、那样弹,会在小处理上留有自由和空间余地,从不会强迫必须怎样做。周先生认为,弹琴应该用最自然最放松的办法来弹奏。虽然先生说话的声音保持在sottovoce(轻声地),但原则性非常强,要求明确。对于作品的风格、版本、指法、谱面上的要求等方面非常严谨,不许有错音、错拍子、错节奏,在这些方面先生绝不妥协。什么事情可以通融,什么事情不可以,表达得清清楚楚。
上主课时,先生会坐在我身边,边唱边耐心地陪我把手指一个一个送进键盘里。
我注意到周先生弹琴时二指时常会翘起来,一开始还刻意模仿过她。后来周先生告诉我:“那是因为下乡插秧时水太冷,冻坏了神经,所以二指弹琴不听话,该它弹的时候却会翘起来。”所以为了躲过这个不听话的家伙,她特意想了办法,给音阶重新编了指法。
跟周先生学的那几年,先生总尽可能地为我创造演奏机会,身体力行带我一同出行,给我弹协奏或者和我一起演奏。从那时起,我们一起去过很多地方,民族宫、使馆、录音棚、外地……直到我出国留学。
德文的缘分
上学时,因为那时候学院里没有艺术指导这个专业,通常谁识谱快,谁就会被临时“抓差”给国外来的专家弹大师课和音乐会。我当时识谱特快,所以中标率极高,有时一周内弹三场不同的音乐会,弹得特别开心。
其中印象深刻的是来自德国布莱梅的歌唱家,叫克劳斯·奥克(KlausOcker)。一天周先生兴奋地告诉我,奥克先生一下飞机就问她,上次跟课堂那个弹得很好的可爱小孩儿,有没有可能两天后给他弹声乐套曲《冬之旅》音乐会?
记得那一堂课,我识谱,周先生坐在我身边,把24首歌曲逐字逐句地边弹边翻译。在先生这样的陪伴下,让一直以很快“拿下”一首作品而沾沾自喜的我,似乎忽然悟到语言、歌词、诗句、内容、音乐、风格、色彩之间丰富多彩的关系。
奥克先生和我的合作从一开始就进行顺利,两天以后的音乐会和之后使馆及外地的巡演,一切都很和谐,我似乎都很懂得他唱的内容,合作默契。这次合作让我受益匪浅,并对德国艺术歌曲、德文产生很大好感。
永远的楷模
从小时候的筒子楼开始,到附小、附中、本科,甚至留学时去了周先生出生的德国,回国后又在先生隔壁的教室,时时听着先生上课和练琴……一切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我似乎可以一直在周先生身边,不断沐浴着这份温暖而充满大爱的阳光,而周先生是邻居家那位慈爱、温和、平常却不平凡的周先生,是中国琴童们的“钢琴妈妈”。
周先生,爱您,感恩您!您在我们心里,从未离开!您身后的事业和生活仍在继续。如您所愿,我们会将您传承给我们的一切,发扬光大,为中国的钢琴事业发展培养更多的人才。
赵聆/文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dgzhengxing.net/wzqdyy/9782.html